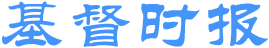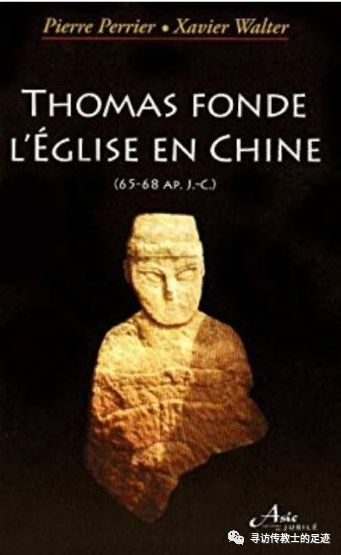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序言
这本书藉着对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崖壁上的人物浮雕的研究,揭示了使徒多马于公元65至68年来到中国宣教,并在中国奠立了中国教会这一事实,比佛教进入中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却被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篡改了,后者也在孔望山崖壁上雕刻了大量的佛教浮雕,企图掩盖真相,并将圣母马利亚抱着婴孩的浮雕形象篡改为佛教观世音的形象,欺骗了历史历代的华夏子孙,使他们不但偏离了真理,而且还误以为佛教是本土信仰,基督教是外来的信仰。
正如圣经所记,耶稣是明亮的晨星,撒旦自称“明亮之星”,假扮“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世人;使徒保罗在宣教途中遇到一位巴耶稣,巴耶稣的名字容易让我们混淆以为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撒旦的伎俩,遗憾的是,撒旦似乎成功地蒙蔽和欺骗了大多数的中国人,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相让我们知道孔望山岩壁上的浮雕人物是使徒多马和他的翻译,还有马利亚抱着圣婴。“他们三个都在那里提醒华夏神州,后者,在祂短暂的尘世生活的第二天,祂也向她表现出了祂的关心。圣婴希望祂的好消息在公元64年被传达给天子(汉明帝)和所有的中国人,从公元65年开始,即在这些西方的希伯来人知道‘光之人’的到来之前,华夏神州就已经有一代人见到并认识祂是谁了。祂希望见证人来到他们身边,只有在祂十二门徒中的多马,用手指证明了所有人通过十字架之救赎而得到的复活的凭据。出生于中东的‘光之人’从公元前5年到30年生活在那里,向每个人展示他对他所有弟兄的神圣关怀。祂死了,复活了,然后升天了,但通过他的使徒,他继续赢得每个人的心——即使他们在地球的尽头。因此,中国在许多国家听到祂之前很久就收到了祂的Word。”
没错,据被尘封在梵蒂冈1700年的一本叙利亚文古卷《智者的启示》记载,来到伯利恒朝拜圣婴的东方博士就是从连云港孔望山出发的中国智者,他们在这个地方守望伯利恒之星的出现已经守望了4000年,他们是塞特的后裔,是‘光之人’的信徒,在他们的这本自传中,是以使徒多马来到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与他们见面,为他们施洗,并差派他们传福音结束的。这两本书互为印证,证实了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就是敬拜上帝的,基督教信仰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土信仰,虽然撒旦用尽心机来掩盖真相,但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在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华儿女回归祖先信仰的时候,就是圣灵活水江河涌流在中华大地的时候,基督的福音要复兴神州大地,迎主再来!
高梓良牧師
于2023年3月10日 多伦多
使徒多马奠立中国基督教会
— 公元65至68年
辨认孔望山中国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浮雕
中文摘要
最近有一项有关公元一世纪浅浮雕的研究,完全以纯佛教起源做背景,这些雕刻在一石崖上仍保持很清晰,地点就在连云港前往中国东汉首都洛阳的古道不远处,我们目前对犹太基督教世界较佳的认知,使我们能够确切地在这崖壁上众多的雕刻人物中将其中两位— 甚至可能三位—的主要人物指认为基督教人物:他们为两位基督教—而非佛教—“使者”到中国使行的见证,这在文献中明确地提到是透过海路来自安息人帝国与印度南方的旅行者,当时陆道的丝路因为战争无止已被切断多年,罗马、安息、中国3帝国主要以海运通商。
如果我们识别出这些人物为安息人雕刻家依照波斯湾附近胡齐斯坦艺术风格所琢出的浅浮雕基督教人物,仔细分析现有的中国文献中提到,在公元50年左右,这些旅行者在中国受到礼遇,离耶稣讲道不到40年的时间,再加上来自考古的其他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罗马帝国东方教会的文献数据之历史价值:安息人或印度传统中提到基督门徒多马于公元52至64年之间的印度北方,继而在印度南方传教,之后前往中国。
孔望山石崖上第一位人物胸前持基督教特色的十字架,为主教准备祝福信者之姿,同时他所戴的犹太祭司长冠帽指明其使徒的任务,第二位人物的右手朝上,结合左手所执一展开的卷轴,依据犹太教传统,为已经透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圣言,确认了他扮演传达和翻译者的角色。此外,这两位人物之间有一代表复活的基督教十字架的表征,其特殊的形象可断代为公元一世纪,另外第三位人物在石崖较远处,宛若从上方眺望这两位传教者,是一抱婴女子,穿凉鞋,双腿折叉,为典型安息人妇女生产后抱子坐姿,与佛教沉思打坐造型大异,而与后世西安附近楼观台纪年650年的大秦景教塔上一残存雕刻类似,代表圣婴降生,同时要指出这三位主要人物的姿态与衣着皆为中东两河流域风格,而非受印度北方贵霜王国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两位使者阿拉米语(古叙利亚语,中文又译为亚兰语,耶稣使用的语言)的名字和中国文献上有关此使命的记载较合适基督门徒多马的使命,由他的合作和翻译者陪同(竺法兰,及类似阿拉米语中的Shofarlan,lan: 为我们,shofar:吹号角传播者),而不是如佛教传统中所说的为宣扬佛教的使命,透过印度西北方的犍陀罗之陆道丝路来到中国,事实上,公元一世纪后半叶之际,这条路当时为持续的战争所切断,此外在中国二世纪末之前还没有其他佛教雕刻出现的证明,同时这些佛像只附属于贵霜王朝的造像风格,大乘佛教教义和新的佛经透过贵霜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于公元135年形成,在犍陀罗和印度西北区发展并推广,将近一世纪后才传入中国,我们知道最初的佛教为小乘,属菁英阶级的信仰。并仅局限于印度河流域上游,大乘佛教经文和最早的佛像雕刻在中国要到公元三世纪才于洛阳一佛寺中出现。
这些雕刻的存在与使徒多马公元65至68年的纪年出使相吻合,就在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耶稣之后—他带有光环、高大、金发、非矮小、也非黑发、非白肤色或棕黑色:是闪族的耶稣,而非佛祖。我们认为这些浅浮雕是为纪念使徒多马来到中国之行所刻,由其随行的雕刻家执行,这个告别仪式一定在他临走之前举办,之后他先经过一个面向浩大东海的日本岛屿,再返回印度东南,回到美拉普拉姆三年后,他于公元72年殉教,其死亡之地点与时间由他的墓地考古和当地及教会传统皆有确切证实。
孔望山石崖上一些雕刻可能在多马离开不久之后所雕的,包括汉明帝之梦和明帝与多马之交谈;佛教主题的雕刻则较晚,时间上差距较久,属犍陀罗风格,包括佛涅盘和其他佛本生故事图像。
我们拥有中国文人在公元一世纪帝王年纪中对此梦和此使命的评注分析,正符合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之宣扬,但其后不再被官方承认,这教会也变得不显张,因而被较晚的佛教传统掩盖起来,我们也可以辨认出这个向中国皇帝传教的基督教使徒团的地点,位于后来盖起的洛阳白马寺之东北边,白马寺的建筑有如中国所有的寺宇,坐南北向,佛教的翻译工作和在中国的奠基,始于白马寺,从三世纪起,延续至五世纪。
然而多马与其陪同翻译者被接见处比白马寺略远,之后并在此处盖了教堂,其祭坛就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木制佛塔的底座。这座木塔于11世纪左右毁于火灾,于12世纪以砖石再重修,这木塔明显地显示古老犹太基督教教堂东西向的余存,有如耶路撒冷首座圣殿的方形结构,每边长八公尺,我们认为应该再重新考虑这佛塔和徐州纪元86年带画像石的墓地(目前基督教的可能性较确实)之考古发掘研究,同时补增对连云港浮雕之分析和断代。
中国第一个基督教社团建立于徐州似乎可能—徐州为南方临海楚国的首都:在明帝之兄弟楚王英的周围形成。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明帝本人接受并皈依这位使者和其随伴者所宣扬的信仰,从洛阳到海边的广大区域,在北方—特别是南方—还有许多有关基督教遗迹(包括十字架象征)的考古发掘,也需要统合这些数据加以分析,特别要提到徐州一公元86年的墓明显与基督教有关,出土画像石上雕有此次出使事迹和礼拜中使用的圣经内容,这些考古遗迹显示出基督教信仰传播之迅速和广泛,在中国境内远超过徐州的范围,明帝周遭的高官感到这宗教危及天子政权,因而废楚王英,并迫其自杀。
我们也可以在文献传统中找到后代的传教使者之名字,并非佛教使者,近似阿拉米语的音译,由此考虑到这个中国基督教会与安息人王国中的基督教东方教会从未中断过关系,直到公元637年透过唐太宗下诏令以官方形式再度出现,并于保存了老子的传说,为道教教义的宣扬基地之楼观台正式设立了基督教传教使徒团的基础,同时允许于中国境内各大城市成立教区。
有唐之际,许多主教区彼此联系密切,当时东方教会以萨珊王朝为基地,得到安息人教士之助,加上通商关系,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拥有教会完整的组织结构,唐武宗灭教,景教遭迫害,被逐的传教士目标转向中国北方游牧诸国,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兴盛之时,他们已大量皈依基督教,并加入其军队,参与建立元朝之功,当时中国的教会拥有五个大主教区和三十多个主教区,到蒙古帝国消失后仍继续存在,附属东方教会,直至铁木真下令屠杀数百万拒绝皈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与巴格达的关系被切断,中东余存的基督徒逃离至库尔迪斯坦山区的阿叙利亚圣地,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东方教会之远东部分拥有百余主教区,有一段时期其教长为一位来自北京的大主教。
我们可以说多马到中国的使命让耶稣的福音于公元70年之前传播至太平洋岸的远东之土,就如公元40年,使徒雅各带着十字架到欧洲大陆西边极端,面临美洲,千余年之后,西方海路传教使命在全世界建立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我们的研究结论希望能够承认耶稣与汉明帝于公元64年的梦中相会,作为中国福音传播的源起象征,同时期,正值尼禄皇帝和其帝国的道德衰微,迫害基督徒,彼得和保罗殉教于罗马。
孔望山石崖上的多马与竺法兰使命类似第三位人物:圣婴降生— 圣母玛莉亚怀抱刚出生的耶稣,带着慈悲的眼光看这两位传教者,似乎在保护他们,直至今日,这项和平的福音传播仍为真理,强大的西方科学与科技如果不适当控制会成为危险,东西方两个古老文明的智慧与文化需要作为世界的典范,如孔望山雕刻上所显示,公元一世纪透过耶稣使徒向古罗马和汉帝国宣示的文明同源可作为我们未来的子孙互相了解的基础。
作者:皮耶·裴歇尔
法兰西学院科学院士
翻译:曹慧中
巴黎国立亚洲艺术—吉美博物馆
使徒多马奠立中国教会
(公元65-68年)
Pierre Perrier, Xavier Walter
黄成璐译1-4章
这是一本考古证实不凡的书,也是记载使徒多马公元65到68年来到中国的文学作品。那是在一个尼禄皇帝残暴不仁迫害基督徒的时代,殉道者彼得和保罗死于他的手下。这本书告知我们,在尼禄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时期,早在使徒多马在三年时间内稳固地建立起教会前,在汉明帝统治时期,耶稣已经出现在中国了。
越来越多更确切的证据不断涌现,在佛教到来前一个世纪,一个来源于犹太基督教而非西方的规模宏大的中国教会已经建立。它穿越几个世纪,直接渗入中国的文化或者通过借用佛教和中国传统智慧知识,让我们可以了解。
祈求天福,是中华帝国在黑暗时代的信仰宝藏,它由以色列通过海上之路传播到中国,然后由丝绸之路复兴,这解释了复兴时期的成功和目前教会根深蒂固的信念。教会如今能给21世纪觉醒的中国的带来好处,通过它,中国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复兴。
Pierre Perrier,
达索航天发展和科研前负责人,福音口头传播专家、技术学院创始人、研究所通讯员
Xavier Walter
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的专家(出版十余部作品),阿兰·佩里菲特前合作伙伴
第一章
研究开端
南京机场烟雾弥漫,我们飞机刚起飞前往北京,我们期望尽早到达以避免错过前往巴黎的转机。我正完成一个任务,它有两个目标:第一,与南京大学的学生召开两次中欧关系框架内的会议;第二,响应中国基督教起源相关问题的科研需求。终于,我坐在了我的座位上,飞机实际起飞时间可以赶上前往欧洲的联运,这使我心安了。
于是,我开始总结这两个任务。对于科学与科技这一方面来说,为了这两场会议,我精心准备了计算机上的幻灯片和默认可能出现问题的答案,除了我需要适应一群年轻的听众以外,会议一切顺利进行,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在我看来还欠佳。我提议了中欧航空领域之间合作的主题,这被接受了。但是这项提案需要更明确的表述。
出于其他目的的邀请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需要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挖掘新的内容,例如最近被挖掘的引入中国的宗教的根源,报纸和网络相互呼应报导了此事,只要满足这一条件,我就接受这两场会议。一些考古学家发现在新纪元的前几个世纪,基督教可能已经进入中国。早几年前,针对此事有过一场辩论。辩论的焦点:人民日报表明在这个方向中如果必须添加决定性的元素,那这将等同于一场地震一样!在公元的前两个世纪,多亏了孔夫子、老子和他们的弟子思考以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个人的责任感,中国在过了三到四个世纪的中央集权发展后进入一个完善的帝国的时期和实行第一个政治制度(三公九卿制),基督教的到来就要比确切记载要早的多,这意味着对正在酝酿的中华文明基础要素对创世纪产生的影响力,有可能是宏大的。
多年来作为研究教会的使徒起源的专家,我必须要了解所有考古学家近年来的新发现,尤其是南京大学大众宗教研究院进行研究得出的两项新发现。因此,我与该学院负责人约了在我特殊的科学和技术的任务完成后会面。会议仅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才组织好。然而,会议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飞机起飞后,我只能从我的公文包中将这些前天向我介绍的“新元素”删去。
可能有两位和尚的地方
正如我所料,人们跟我讲过,所做的研究都是沿着“海上之路”展开的,“海上之路”汉朝古都(长安,然后洛阳)和商业港口连接起来。这个“海上之路”在到达连云港之前经过开封和徐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经贸活动。
在南京大学的大众宗教研究部,有关开封的讨论被掩盖了:当时这位专家生病了,但她的书有英文版本。基于口头传统的方式,这些书主要讲了犹太人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开封(河南)的事迹。曾经有人告诉我,二十年前,在一个港口附近发现一些足迹,最近又被重新评估。如果我们沿着古“海上之路”一直走向内部,我们首先经过两个场所,在岩石上有修剪过的两个纪念建筑物,这可以追溯到第一位皇帝的时期,即秦始皇(221-211),和代表着一个携带者金字塔和蟾蜍的大象……它们象征着什么呢?大象会让人想到港口把中国黄河河口泛滥的河岸与印度相连接吗?大象——象字——在新石器时到就存在于中国的北部,它的体型刻在了一些商代青铜器上(公元前十五世纪直到十一世纪)。传说中神话般的统治者舜把大象拴在犁上,汉末的文学将此比喻成战斗的野兽。中国像是力量、智慧、睿智和谨慎的象征。这难道也是印度的形象吗?公元一世纪末,这很难说。那么蟾蜍呢?它在中国则代表着财富和居住在月球上的人……
这条路一直往西行,围绕着一个名为“孔望”的小悬崖(即孔望山),在山上,植被此前已被砍伐一空,随后一世纪山上的浅浮雕摩崖像才清晰可见。雕像周围被许多后来新添的人物雕像围绕着。如果需要离开港口或者取道前往京都,首先可以在峭壁左侧找到最近科研发现的三座雕像,有两座为最古老的和最大的,还有第三座雕像,稍微小一些。它们分别代表着三个人物,有两个造像是耸立的,还有一个风格一致,但离内壁较远,它所处的位置更高,平躺着,或者呈现出延长的姿态。人们向我展示了这些雕像,并向我保证这些人物是公元一世纪佛教到达中国后有关口头传教的铁证。随后,他们明确指出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日期,为笔头明确记载的日期:65年。此外,传说提到在一世纪应汉明帝之求,有两名和尚来自于印度到了中国,因汉明帝于64年做了一个梦,在他的床边,出现了一个人,个子很高,因此不像是中国人,更像是西方人,其欲解梦,便邀请了两位和尚。
但是!第一位和尚手里拿着十字架!
第一轮研究的前夜,在展示前两个所谓“和尚”的人物造像的照片时,我并没有掩饰我的惊讶。很明显,第一个人物造像是最大的,实际上相当于人类的身高,在右手近胸脯的位置拿着一个十字架。在他身旁,系第二个人物,非常出类拔萃,穿着非中式服装:他以证明真理的姿态敞开右手,左手上拿着卷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雕刻已经慢慢淡化。
在随后漫长的讨论中,这些学者不懈坚持声称,根据他们的分析,这两座雕像是关于佛教徒和尚的。我不得不坦白,说服他们承认这更像是他们的猜想,因为无论如何,他们决不能认为第一位人物造像在胸脯旁手持十字架这一现象是次要的。十字架并非是衣服造型的结果,因为它右手持着的十字架,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超出了衣服的边缘和裁缝。十字架展现出了一个简单的中心雕刻,佩戴者的姿势给十字架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东方的主教在天主教会举行礼拜仪式的庆典活动时候惯用的姿势,这也是我们现有的旧肖像集证词中最认可的姿势。这只可能是一个拿着十字架的基督祭司,旁边是他的辅祭,造像小一些,右手证实了他左手的卷纸上所写的会规信仰,展现出来如同传统的基督教肖像集描写的那样,这被后人证实过的。
您说公元65年?
此外,我为刻在悬崖上事件的时间很惊讶:公元65年。为什么会惊讶呢?我把它归因于我最近的按时间顺序的调查,这份调查是基于我在印度南部向马拉巴尔的基督徒收集的口头记录,他们讲诉了一系列的事实,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64年,根据印度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口诉,使徒多马结束了在南印度传教使命后,在离开迈拉波拉姆(马德拉斯附近)之前,来了中国。
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现以及其与我致力于完成使命的工作即研究使徒多马走向东方出现的共同点变得十分离奇,也使我从这场辩论中论点的困惑深渊中逃离出来,这些论点声明,雕刻在岩石上的浅浮雕是第一批佛教徒在中国传教的证词。为什么如此明显的基督教性质的肖像却这么难被认出来呢?由于我对中国佛教并不了解,我困惑不已。在飞机上,由于他们给了我照片的复印件,我开始重新研究照片上的这两座造像。又因为在我快离开的时候,他们才给了我第三座造像的照片,我迟了一些才看出来这三座造像的联系。
还有一个女人!
一眼看去,第三座雕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因此可以理解,尽管我们可能明确猜到这是一个女人的头,精致的头发,或多或少有一世纪下半叶中国女人的味道,例如,前天下午在南京博物馆观察到这一时期的雕像,尤其是那些女人的雕像,她们的发型和穿着都和这里颇为相似。第三个人物的浅浮雕雕像在我看来已经十分明确了。但是它意味着什么,不知所以然,她没有在看其他两个人物吗?我没有立马观察到更多的东西,我被迷住了,就像之前对那个高大的人物造像痴迷一样。
我更仔细地想到了一个人物的发型,那个我看过的教徒的发型,我认出了在头巾上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十字架,由石头或者刺绣制成,固定在发带的上方显眼的位置。这个发型的问题是:“如果我讲它与其他同期在南京博物馆看到的男人的发型进行对比的话,这不可能是一个中式发型,更不可能是印度式发型,因为他们不能带一条如此明显的发带,除非为个人所用。
到达北京机场后,留给转机的时间非常少,那么迟到就显得举足轻重了,这迅速将我的思绪扯回到二十一世纪和法国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我得知法国航空的航班因乘务员罢工将延误,我注意到这场“社会运动”造成法式的混乱,甚至是意大利式的,因为相当一部分乘客是意大利人,因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回到他们的祖国而十分沮丧。法国和意大利的中转站是巴黎戴高乐机场。我又陷入了法国人的混乱中,这些无法预料的举动成功阻碍了快速转机的通道。快速转机是认真的研究和法国航空业高技术的成果,这个也是我作为工业研究和发展的高级经理贡献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的地方。
但是法国也是一个卓越的地方。在非宗教化的错误后,基督教的起源逐渐明朗起来:犹太-基督教根据巴勒斯坦考古学揭开面纱,由红衣主教达内尔鲁深入研究,他的人类学归功于朱塞斯神父。在《东方教会》中有一段他的口述由红衣主教提斯朗(Tisserand)和皮尔·陶维里耶(Pr. Dauvilier)揭露:“东方教会的圣土由使徒巴多罗买、圣犹大·多马建立(西罗马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范围外),在几个世纪内,形成了帕提亚教堂和中国和印度天主教教堂的关系。
立场声明
基督时报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基督时报保持中立。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 (021-6224 3972) 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ChTimes)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